

日照日報/日照新聞網訊 初見王懷智老人,他正在家中安詳地翻閱著雜志。臉上的從容和矍鑠似乎寫滿了歲月對他的眷顧。歷史長河悠悠淌過,在王懷智的人生畫卷上暈染出波瀾壯闊的色彩。
這位曾握槍桿子護家國、執鋤把子濟蒼生的99歲老者,把烽火歲月的熾熱、建設年代的厚重,都釀成了日常里的從容。從19歲那年初見硝煙,他的生命便與時代同頻共振,每一道皺紋里都藏著星辰,每一寸筋骨中都立著山河。

青年王懷智
個人簡歷
王懷智,男,1927年生,1946年3月參加革命,194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先后擔任自衛隊隊長,高密縣康莊區區長、書記,膠縣北都區黨委書記,膠州地委宣傳部副科長,五蓮縣委文教部副部長,五蓮縣委宣傳部副部長,五蓮縣許孟公社黨委書記,五蓮縣農機局局長,五蓮縣水利局局長,五蓮縣文化局局長等。1987年10月離職休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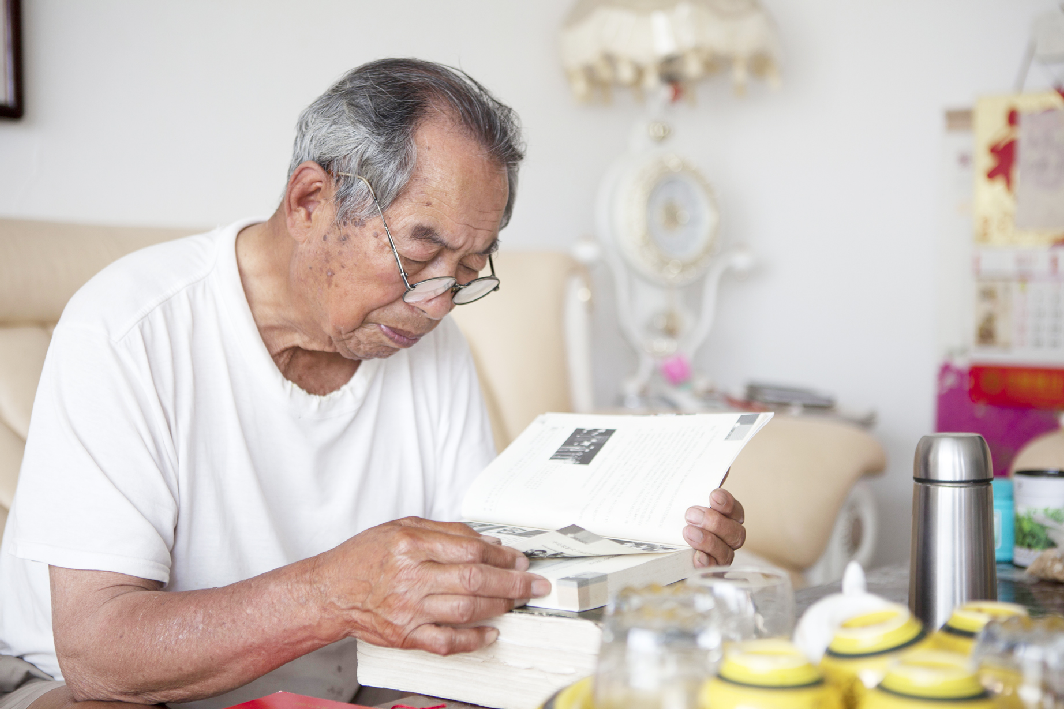
王懷智每日讀書
槍桿子上的青春:從文書到“護城人”
1946年的高密鄉下,19歲的王懷智攥著鋤頭的手第一次握住了筆。彼時解放區剛立穩腳跟,路條是通行的“命符”,兒童團握著紅纓槍在路口站崗,而他這個“讀過書的娃”,成了方平區寫路條的文書。
“字要寫得正,章要蓋得穩,寫錯一個字,可能就耽誤大事。”他在糙紙上一筆一劃寫清姓名、去向,那些帶著墨香的紙片,后來都成了戰士和百姓眼里的“通行證”。
可亂世里,筆桿子護不住家國。沒過多久,王懷智就扛起了槍。先是當村干部,再是基干班班長、自衛隊隊長,最后加入地方武工隊。“那會兒武器可雜了,德國手槍、意大利機槍,我扛的是機關槍,隊伍里的‘重火力’!”說起這段,他滿是皺紋的手忽然繃緊,像還握著冰冷的槍身。
武工隊的對手是“還鄉團”,那些卷土重來的地主武裝心狠手辣,“夜里睡覺都得睜只眼,他們敢摸黑偷襲,我們就敢硬碰硬。”他說自己也怕過,可看到鄉親們藏在門后怯生生的眼神,“怕也得往前沖。”
真正讓他記了一輩子的,是高密城解放戰。1946年秋,周邊縣城接連解放,殘敵像受驚的兔子般“龜縮”進高密城。正規部隊圍城七天,王懷智帶著地方武裝守在外圍,“就像扎籬笆,一只鳥都不能讓飛出去。”第七晚總攻打響時,他正趴在城東的土坡后,看東翼炮兵率先打破夜空。“炮彈拖著紅光飛過去,城墻‘轟隆’一聲就塌了塊角!”兩個小時的炮火照亮了半個天空,東南角的缺口剛被炸開,戰士們就像潮水般涌進去,沒多久西城墻也破了。“天亮時,城里的紅旗一升,我們都在坡上跳著喊,眼淚混著汗往下流。”

老照片

王懷智在膠縣
車輪與堤壩:民生大地上的實干者
1948年的秋夜,淮海戰役的炮聲還在遠處悶響,王懷智正騎著自行車在月光下穿行。彼時他已是高密縣康莊區區長,帶著“康莊大隊”的1000多人、500輛獨輪車,要把15萬斤糧食送往前線。隊伍太長,白天走就是活靶子,只能靠夜色掩護。每天清晨,他都要冒著頭頂盤旋敵機的危險,騎車探路,“哪里有溝,哪里有橋,哪里能躲飛機,都得記在心里,畫成圖給大伙。”
那半個月,他成了隊伍里的“陀螺”。獨輪車排開有二里地長,他夜里要從前頭跑到后頭,再從后頭奔回前頭,“看三次前頭,查三次后頭,就怕有人掉隊,怕糧食出岔子。”歷時半個月的時間,“康莊大隊”將所有物資安全送達。
槍林彈雨里闖過來的人,到了和平年代,把勁兒都使在了泥土里。1950年,王懷智任膠縣北都區黨委書記。盛夏時節,暴雨連天,五尺河的洪水漫過田埂,一米多深的水把莊稼泡得發漲,百姓蹲在河堤上抹眼淚。王懷智蹲在水邊看了三天,忽然折了兩根高粱秸,一根插在河里,一根插在地里。“就瞅著那秸子露出水面的長短,原來河里水位比地里還低!”
他拍著大腿喊,“扒壩放水!”村民們半信半疑,跟著他挖開河壩,地里的洪水“嘩嘩”往河里流,沒幾天田就露了出來。那年秋天,原本只能種高粱的地里,竟長出了沉甸甸的玉米,百姓提著新收的糧食往他屋里送,他笑著擺手:“我是黨員,就該干這事。”
1973年到五蓮縣水利局工作時,他成了五蓮縣的“活水文圖”。上百處水域,哪個河深幾尺,哪個壩能扛住多大水,他都像刻在腦子里。后來到文旅局,又領著人建起圖書館、電影院,那些建筑成了縣城的地標。

全家福(攝于2000年春節)

2013年9月,王懷智和愛人張建民(張建民,1949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)
家風如燈:皺紋里的紅色傳承
夕陽西下,傍晚的余暉透過窗,照在王懷智家里的全家福上,給相框罩上一層金邊。相片里,一大家人站成幾排,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微笑。“全家幾乎都是黨員,倆兒子當兵,一個孫子也當兵,一個孫子穿警服,都是為人民服務的。”說起這些,79年黨齡的王懷智眼里的光比夕陽閃亮。
兒子們記得,父親總把“兩不怕”掛在嘴邊: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。不能考慮個人,要為大局想。”他用一輩子寫下的“一身正氣,兩袖清風”,證明這不是空話。
離休后的王懷智,生活過得比年輕人還充實。天不亮就起來讀書看報,字認不全的就查字典,一本厚重的《辭海》被王懷智翻了上萬遍,膠帶粘了又粘;偶爾約著老友去打門球、下象棋、釣魚。可他最喜歡的,還是給孫子們講紅色故事——那些泡發在歲月長河里的記憶一遍遍被打撈起,變成了這個家庭中代代傳承的深刻印記。他講得慢,孩子們聽得靜,月光透過樹葉灑在他臉上,那些皺紋里仿佛藏著整個烽火年代。
如今99歲的他,能騎著電動自行車去買菜,隔三差五兒子們還陪同著他去釣魚。有人問長壽的秘訣,他嘿嘿笑:“心里干凈,干活踏實,啥愁事都擱不住。”
雨過天晴的夏日,天空湛藍如洗。風吹過路邊的柳樹沙沙作響,像在說:這世間最動人的風華,從不是青春的模樣,而是把一輩子交給家國的赤誠。王懷智坐在海邊垂釣,看著遠處的山——
年輕時扛槍保衛的山河,中年時揮汗建設的家園,老年時守護的家風,都在暮色里漸漸溫柔。從19歲到99歲,他的人生像一支燃燒的紅燭,在烽火里照亮過前路,在建設中溫暖過民心,在歲月里傳承著火種。他和無數像他一樣的老黨員,早已把自己活成了路標,讓后來者知道,來路有多不易,前路該往何方。(日照報業全媒體記者 田文佼 通訊員 宋曉磊 報道)
